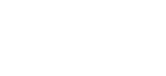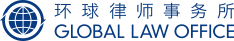一、AI大模型本身所涉的不正当竞争问题-抖音“变身漫画特效模型”诉B612咔叽“少女漫画特效”案[1]
该案为国内首例AI大模型本身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案件。该案原告主张被告同时构成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关于著作权侵权,一审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变身漫画成像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从而未认定著作权侵权。二审中双方均未就著作权侵权问题上诉,故二审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未再就此评价。关于不正当竞争,该案明确竞争性利益的客体为AI大模型的具体结构和参数,而非基于AI大模型的应用产品,未经许可使用他人训练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一)基本案情
-
原告主张的权益基础:2020年6月15日,原告抖音安卓端APP上线“变身漫画特效”,该特效可以将用户实时拍摄的照片、视频转换为漫画风格。原告主张变身漫画成像是美术作品、视听作品(变身漫画成像生成过程表现为风格设定、风格化量产、模型训练、用户生成四个阶段,此过程体现原告的独创性选择与判断);该特效模型还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保护的竞争利益。
-
原告主张被告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被告B612咔叽安卓端APP于2020年8月4日上线的“少女漫画特效”复制、传播少女漫画成像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就变身漫画成像享有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 原告主张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以抄袭变身漫画特效模型结构和参数的方式使得少女漫画成像与变身漫画成像高度近似,该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一审法院关于变身漫画成像不属于受著作权法所保护作品的认定
1. 法院查明原告变身漫画特效模型(结构和参数)与成像形成的过程为:
(1)风格设定阶段(2019.8-2019.9):该阶段最终确定变身漫画成像以“像”和“美”为标准。“像”包括:五官完整、位置基本匹配,无扭曲;装饰物品完整;服装、背景颜色基本还原;发型、脸型基本一致;还原、均匀发色和肤色。“美”包括:手势基本还原;妆容还原或添加额外适合妆容;整体饱和度、对比度符合一般动漫标准;风格化色调;还原面部表情或产生额外适合表情;夸张头发的彩色倾向。
(2)风格化量产阶段(2019.9-2019.11):以“像”和“美”为标准,聘用手绘师对照Faceu软件公开的真人照片绘制50696张漫画,该等漫画数据为模型训练阶段的全部漫画数据。
(3)模型训练阶段(2019.11-2020.6):变身漫画特效模型是在 Cyclegan 模型基础上调整模型结构及参数并利用手绘师绘制的漫画数据与相对应的真人数据予以训练。具体过程表现为先输入真人数据,得到不符合预期的图片,进一步调整模型结构、参数,反复输入成对数据训练,当模型可以生成符合预期的效果时确定最终的模型结构和参数,变身漫画特效最终选用模型为PIX2PIX模型。原告证人表示:Cyclegan 模型未考虑手机端的实时效果、优化空间很大,PIX2PIX模型与该模型已经没有关系。
(4)用户生成阶段:原告认可不同用户使用变身漫画拍摄同样的人像和视频的成像效果相同。原告在该案聘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均表示模型固定后输入内容相同则输出结果大致相同,即使输入相同的内容后呈现的输出结果存在细节差异,差异部分亦来源于模型的预先设置。
2. 法院认为原告在变身漫画特效形成的四个阶段的行为均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行为,变身漫画成像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理由在于:
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创作行为既不能是单纯积累素材、数据、创造生成工具的行为,也不能是按照既定的规则机械地完成一种工作,缺乏创作空间的行为。具体到原告主张的变身漫画特效的创作行为:风格化量产阶段的漫画创作行为属于为训练模型及最终实现统一的变身漫画成像风格所做的数据积累工作;模型训练阶段中优化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属于为变身漫画成像创造生成工具的行为,原告只能设定变身漫画特效生成的风格;用户启动变身漫画特效并拍摄的行为属于为生成过程提供被转换内容的活动,变身漫画成像生成阶段真人与成像效果存在唯一或有限的对应性,无法体现自然人的思想、情感和个性。
(三)两审法院关于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认定
1. 二审法院查明大模型由结构和参数组成。
(1)模型:是计算机从大量训练过程中统计到的输入和输出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使模型可以对其未曾接触过的但分布相似的数据进行预测或决策。
(2)模型由结构和参数组成:模型的结构是指模型各个组成部分的连接方式、结构、数量、位置和顺序等,模型的组成部分可以包括不同的层(如卷积层、BN 层、非线性激活层)、升采样模块、激活函数等等。模型的参数是通过大量训练和调整形成的成果,是具体数值,如卷积层的输入数据的通道数、输出数据的通道数、卷积核的大小、卷积运算时的步长、是否使用偏置以及对图片的填充等等均以参数表示。
2. 二审法院依次审查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认定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
(1)该案原被告之间具有直接竞争关系。
(2)原告就变身漫画特效模型(结构和参数)享有竞争利益,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法院将变身漫画特效本身作为原告竞争利益的认定。
二审法院认为原告享有竞争利益的客体为变身漫画特效的模型,具体为模型的结构和参数。具体而言:原告为研发变身漫画特效模型投入大量经营资源、变身漫画特效的成像效果也经历了不断优化过程,而变身漫画特效模型经过数据训练和调校后的参数与结构使得用户在使用抖音APP时能生成与真人具有对应关系的动漫形象,为原告取得了创新优势、经营收益和市场利益。[2]
二审法院进一步明确,原告主张的是变身漫画特效的模型(结构和参数)为其竞争利益,而非基于该模型推出的特效应用产品,因此一审法院仅基于变身漫画特效本身论述原告是否具有竞争利益与原告的主张不符、应予纠正。
(3)被告的被诉行为违反法律和商业道德,具有不正当性。
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经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为该领域的商业道德,被告违反了该商业道德。被告的少女漫画特效上线时间晚于原告的变身漫画特效,具有接触可能性;经比对,二者构成实质性相似,被告主张其未使用原告的变身漫画特效模型但未对二者之间在结构、参数等细节方面的极高相似度作出合理解释。被告的行为为其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短时间内打破了原告形成的竞争优势和技术壁垒,并在原告模型上线后不久与原告竞争用户和流量,具有不正当性。
(4)被告的被诉行为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替代效果。
被告的被诉模型与原告的模型效果非常相似,且二者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提供产品的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因此相互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作用,可以认定被告的少女漫画特效模型对原告的变身漫画特效模型具有较强的分流作用,给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损害。
(5)被告的被诉行为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审法院认为被诉行为直接扭曲了变身漫画特效模型的正常供求机制,间接阻碍了原告通过变身漫画特效模型获得竞争收益、收回创新投资,造成了该领域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如不进行规制,则无法恢复被扭曲的供求机制和创新机制,无法发挥正常的供求机制和创新机制作用。长远来看,如不对被诉行为进行规制,将使得通过训练数据的人工智能模型经营者不是寻求正当方式研发改进模型,而是通过被诉行为这种不当手段获取并商业化利用他人模型,导致市场激励机制失灵,扰乱了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此外,被诉行为如不被制止,会影响到数字技术创新企业的创新产品推出,影响消费者未来的选择空间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被告的被诉行为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知识产权专门法等之外的情形,因此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
(四)该案给大模型权利主体的启示
1. 对于大模型权利人而言,首先需要注意其深度训练后的模型是否已产生了区别于所使用的开源模型的实质特征。
基于前述案例可以看出,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现阶段更为可行的保护其就大模型所享有权益的路径。不容忽视的前提是权利人能够论证其通过自身的研发等投入使得其主张保护的大模型已经产生了区别于所使用的开源模型的实质特征。该案中,原告通过证人(其公司技术人员)和专家辅助人的方式证明:其最初选用的Cyclegan开源模型的基本框架相同、进行深度训练后的模型则会有所不同,而原告最终的变身漫画特效模型已经与最初选用的Cyclegan模型没有关系。
2. 对于大模型权利人而言,注重其对模型结构和参数反复调校证据的留存是论证其享有竞争利益的关键。
该案中,原告提交了《外包服务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手绘师《劳动合同》、飞书动漫修图群组记录、研发日志等证据拟证明其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对变身漫画特效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进行了反复训练和调校,这是原告论证其对变身漫画特效模型结构和参数享有竞争利益的关键。
3. 关于被诉行为的不正当性,法院参考著作权案件中的“接触+实质性相似”认定模型结构和参数的抄袭可能性,权利人维权时需从此角度进行准备和举证。
关于接触,被告的少女漫画特效发布时间晚于原告变身漫画特效模型的发布时间,且原告变身漫画特效模型在抖音APP终端本地运行,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取模型本身并解密,从而获取模型的结构和参数,法院据此认定被告具有接触原告模型的可能性。
关于抄袭可能性,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专家比对意见显示,原告变身漫画特效模型与被告少女漫画特效模型的结构、卷积层数据、分辨率、激活函数及模型结构中的整体网络结构完全一致;非相邻子网络之间的连接关系、相互连接的非相邻子网络的结构、卷积层层数、升采样次数位置均一致;双方模型升采样方法不同等少量差异对最终漫画效果的影响为微小或无。被告未提交其独立研发的证据(模型训练及数据集证据)。法院认定被告少女漫画特效模型有较高可能性抄袭了原告变身漫画特效模型,二者在技术实现方面具有高度同一性。
(五)该案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大模型训练数据的合法性是否影响竞争利益的获得?
该案被告抗辩原告使用非法获取的人脸数据进行训练,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由此获得的竞争利益不属于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保护的合法权益。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用于模型训练的数据合法性问题不影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下评价被告的被诉行为,具体论述为:“抖音公司用于模型训练的数据合法性问题不影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则效应下对亿睿科公司的行为进行评价。”
二审法院则认为竞争利益的获得本身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但其认为被告未证明原告获取人脸数据的行为与其使用何种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直接相关,因此未支持被告的抗辩,其具体论述为:“抖音公司仅主张变身漫画模型构成其竞争利益,而亿睿科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抖音公司获取人脸照片数据的行为与该公司选择何种人工智能的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直接相关。”
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在原告模型训练阶段,需要根据手绘师绘制的漫画数据和真人数据对模型的结构和参数不断调整最终确定选用的模型,且如前所述,法院查明手绘师对照Faceu软件公开的真人照片所绘制的50696张漫画为模型训练阶段的全部漫画数据。原告也在二审中提交了两份证据(FaceU软件《产品体验报告》、当前版本FaceU软件中“拍同款”模块可以看到用户2019年9月25日上传的公开特效照片),用以证明其变身漫画模型训练数据中的真人数据系用户自行公开或合法公开的数据;二审法院也查明了2019年版本的FaceU软件具有用户公开照片的选项和路径。
本文认为,该案在案证据已经证明了原告变身漫画模型的结构和参数事实上与被告抗辩的真人人脸数据应存在关联性,因此二审法院以被告未证明关联性为由未予支持被告的抗辩,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或之嫌。本文认同二审法院关于竞争利益的获得本身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主张,但二审法院应在查清上述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此种情况下原告对其变身漫画特效模型是否还享有竞争利益,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二、AI大模型相关商标侵权问题——“通义千问大模型商标侵权纠纷”案
尽管目前生成式AI最典型的纠纷和争议集中在著作权领域(参见本系列文章中的前三篇),但已经有相关的商标侵权案件出现,如“通义千问大模型商标侵权纠纷”案[3]。该案为全国首例AI大模型商标侵权案件。不过该案争议所涉法律问题尚属于常规的商标侵权判定。相信随着生成式AI的不断发展,未来关于商标性使用的判断、相关商品及服务类别和属性的判断等都会成为受关注的问题。相关主体应保持关注,提前识别潜在的商标侵权风险,合法合规经营。现对该案梳理介绍如下:
(一)基本案情-商标侵权部分
1. 原告主张的权利基础:“通义”商标。
原告主张“通义”是其大模型统一品牌,“通义千问”大模型是由原告共同运营的一款人工智能工具,覆盖语言、听觉、多模态等领域,能够实现多轮对话、文案创作、逻辑推理、多模态理解、多语言支持等多种功能。
原告在诸多类别上申请和注册了多项商标,包括2022年12月7日获准注册的第9类65061853号、第38类65045694号、第42类65061875号的“通义”商标(以下统称“权利商标”)。其中,第65061853号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项目包括计算机软件、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数据处理设备、计算机外围设备等;第65045694号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项目包括信息传送、计算机终端通信、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等;第65061875号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项目包括计算机程序和数据的数据转换(非有形转换)、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软件即服务(SaaS)、电子数据存储、云计算等。2023年10月31日,通义千问正式发布APP并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上线。
2. 原告主张被告的商标侵权行为:
被告在其运营的西西软件园中提供“通义千问”和“通义听悟”的软件下载服务,在网页标题链接、软件名称、安装后的APP名称或插件名称、软件介绍、软件截图等处使用“通义千问”“通义听悟”字样,并设置通义千问下载专区,在专区标题、专区内软件名称、图片等处使用“通义千问”字样。
(二)法院认定:被告构成商标侵权
1. 被告提供被诉软件的下载服务与原告权利商标核定的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
原告第65061853号“通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项目包括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第65045694号“通义”商标核定使用服务项目包括信息传送、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提供数据传送服务;第65061875号“通义”商标核定使用服务项目包括软件即服务(SaaS)、通过网站提供计算服务和计算机信息、云计算。
被告在其运营的西西软件园中提供“通义千问”和“通义听悟”软件的下载服务,属于在网络上提供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手机应用软件,该行为所涉商品和服务类别与第65061853号、第65061875号“通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类别相同,与第65045694号“通义”商标核定使用服务类似。
2. 被告对被诉标识“通义千问”“通义千悟”的使用具有标识该商品或服务内容及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性使用。
3. 被诉标识“通义千问”“通义千悟”与原告权利商标“通义”构成近似。
被告被诉侵权行为中使用的“通义千问”和“通义听悟”包含了权利商标“通义”二字,“通义”是原告的大模型产品,是其“通义千问”和“通义听悟”产品的核心要素,该部分构成被诉侵权标识的主要识别部分,且原告亦提交了证据证明其“通义”商标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商标中最具显著性部分相同的情况下,被诉侵权行为使用的上述标识与原告权利商标构成近似。
4. 被诉行为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
被告提供的软件并非原告的官方软件,其未经许可在其运营的西西软件园中提供“通义千问”和“通义听悟”软件的下载服务,并在网页标题链接、软件名称、安装后的APP名称或插件名称、软件介绍、软件截图等处使用“通义千问”“通义听悟”字样,并设置通义千问下载专区,在专区标题、专区内软件名称、图片等处使用“通义千问”字样,与原告权利商标近似,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导致相关公众误以为涉案软件系由原告提供,或被告与原告具有授权、合作等特定联系。
5. 被告抗辩被诉链接下载后跳转至原告官方网站,其不属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被诉商标不构成侵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被诉行为发生时,原告尚未正式对外发布相关软件官方app版本,且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述下载后的app并不能完整体现原告涉案软件,且该被诉侵权行为可能导致用户体验感及原告案涉商标品质保障功能的降低。被告提供下载的软件并非原告的官方app,且其提供的部分链接点开后显示其他软件的下载界面或下载安装后显示与涉案软件无关的app,被告主张其系转发的第三方链接,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
(三)关于不正当竞争
除了商标侵权,原告还主张被告存在两项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一,被告在其上传及发布的APP命名中使用“通义千问”字样涉嫌仿冒原告具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产品名称“通义千问”或其他仿冒行为;其二,被告在西西软件园中描述“通义千问”APP是原告官方版的APP,但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原告从未发布、传播过APP版本的产品,被告的行为属于虚假宣传。
法院认定:被告使用“通义千问”的行为已被认定为商标侵权,不再重复评价商品名称仿冒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的被诉宣传行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存在利用其宣传行为以提高其网站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攀附行为,极易引发用户误解其提供的软件来源于原告,该等行为在为其获得商业机会的同时,给原告软件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不利影响,损害了原告的商业声誉和作为经营者的竞争优势和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
注释:
[1]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3)京73民终380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5民初71391号民事判决书。
[2]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具体论述为:“在案证据显示,在模型风格设定过程中,抖音公司通过对市场上大量动漫形象分析对比,从多名手绘师中广泛收集漫画数据风格,最终从中选出最终设定的风格,并根据该风格确定漫画数据的具体绘制标准和要求。在训练数据的形成阶段,抖音公司聘请十余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漫画数据的具体绘制标准手工绘制漫画图,用于模型的学习训练,并在模型训练过程中根据模型的输出结果调整画法、再次绘制漫画图,用于模型的训练和提升,最终形成五万余张漫画训练数据在模型研发阶段,在抖音公司模型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模型结构、模型参数、反复输入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并通过画法调整、增加数据量,算法进一步调整等方式解决中间模型的效果瑕疵问题,使得模型效果趋于接近目标。在模型效果确认阶段,从迭代速度极快的众多模型版本中挑选出最终确定的模型。”
[3] 参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鄂01知民初48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