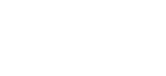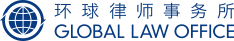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于2025年6月4日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企业在美涉及的新立案及已结案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总量为1856起,其中专利诉讼案件为870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870起专利诉讼案件中,涉及跨境电商的专利诉讼案件达410起。这组数据凸显了专利纠纷,特别是跨境电商领域的专利纠纷,已成为中国出海企业在美面临的核心知识产权挑战之一。
在此背景下,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Declaratory Judgment Action for Non-Infringement of Patent)逐渐成为中国企业主动应对美国专利侵权指控、消除法律状态不确定性、保障商业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维权措施。此外,被控侵权的中国企业通过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可以自主选择对其相对有利的管辖法院[1]和诉讼启动的时间。因此,近年来中国企业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呈现显著增长态势。
本文聚焦美国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结合最新司法实践与法律规定,系统梳理与分析该诉讼的核心法律问题,包括管辖权规则、起诉前提条件、诉状充分性要求、举证责任分配、强制性反诉要求以及其与美国多方复审专利无效程序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中国企业未来在美国运用此诉讼策略提供实务指引与参考。
一、美国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管辖
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的前提是原告须证明受理案件的美国法院具有事项管辖权(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和属人管辖权(personal jurisdiction)。此外,原告还需确定合适的审判地(proper venue)。事项管辖权是指法院对案涉法律事项具有审理权限,属人管辖权是指法院具有针对诉讼当事人作出有约束力判决的权力。理论上讲,属人管辖权既包括对原告的管辖权,也包括对被告的管辖权。但由于原告会主动选择法院并同意法院对其行使管辖权,因此,实践中属人管辖权主要关注的是法院对被告的管辖权。
(一)事项管辖权
《美国法典》第28卷第1338条(28 U.S. Code § 1338)规定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于依据国会有关专利、植物品种保护、版权、商标的立法提起的民事诉讼具有初审管辖权。由于美国专利法属于联邦法,规定在《美国法典》第35卷中,因此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与专利法有关的诉讼具有管辖权,但不是所有与专利有关的诉讼都与联邦专利法有关,比如根据许可合同产生的专利许可费纠纷,通常就属于州法院管辖的范围(但专利合同纠纷满足联邦地区法院的管辖要件的,也可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涉及美国专利法相关内容,因此,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的一审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进行。此外,根据《美国法典》第28卷第2201条(28 U.S. Code § 2201,也即美国《宣告式判决法》),美国法院对其管辖法院内的“实际争议”(actual controversy)案件,可以宣告并判决任何利害关系方的权利和其他法律关系。即只有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中被控侵权方与专利权人之间存在“实际争议”,才能由相应美国法院管辖,“实际争议”的具体认定请详见“二、美国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被受理的前提条件——实际争议”。
(二)属人管辖权
对于属人管辖权而言,其分为一般属人管辖权(general personal jurisdiction)和特殊属人管辖权(specific personal jurisdiction)。法院只需确立其中一种管辖权,即可对被告行使属人管辖权。一般属人管辖权是指因被告注册于或主营业务所在地位于法院所在州,该州所在地法院取得的管辖权,或者在特殊情形下,被告在法院所在州有非常实质性的业务,以至于视同其就是该州的公司(如在该州的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程度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从而确立该州所在地法院对其的一般属人管辖权。特殊属人管辖权是指根据联邦法院所在州的长臂管辖规定,被告在法院所在州实施了特定的行为,且该行为引发(arises out of)原告的诉讼或与原告的诉讼相关(relates to)的情形,法院辖区(forum)和被告之间存在最低程度的联系(minimum contacts),且该最低程度的联系符合美国宪法正当程序条款要求的公平与实质正义的传统理念,从而在该州所在地法院取得管辖权。
在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中,被控侵权方为原告,专利权人为被告。实践中,对专利权人的一般属人管辖权经常难以适用。若建立对专利权人的特殊属人管辖权,需证明:(1)法院辖区(forum)和专利权人之间存在最低程度的联系(minimum contacts),即专利权人在法院所在州实施了救济和保护专利权的行为(enforcement of the patent),且前述行为引发被控侵权方的诉讼或与被控侵权方的诉讼相关。但是,若专利权人仅仅是进行自身的商业化努力(如销售产品或许可专利),而非救济和保护专利权,则无法建立对其的特殊属人管辖权(Radio Systems Corp. v. Accession, Inc.案[2])。(2)法院行使特殊属人管辖权合理且公平。通常而言,当满足“最低程度的联系”要件时,管辖权的行使即推定具有合理性,被告需提出有说服力的主张证明法院行使特殊属人管辖权不合理。法院也会结合案件事实,综合考虑以下五个因素进行判断:(1)被告的诉讼负担(主要考量因素);(2)法院所在州对裁决争议的利益;(3)原告获得便捷且有效救济的利益;(4)州司法系统实现争议最有效解决的利益,也即支持和解的专利政策(settlement-promoting policy),应当允许专利权人向特定法院辖区的一方发送通知函以尝试解决纠纷,而不必因此在该法院被提起诉讼(Red Wing Shoe Company, Inc. v. Hockerson-Halberstadt, Inc.[3]案);(5)各州在推进基本实体社会政策方面的共同利益。[4]
通常而言,就特殊属人管辖权而言,仅发送停止侵权函(a cease and desist letter)或侵权通知函本身即可以在法院辖区建立最低程度的联系。当然,如果停止侵权函或侵权通知函随后引发双方在连续时间段内的多次通信,包括但不限于向被控侵权方提供和解协议、威胁诉讼或专利许可(Trimble Inc. v. Perdiemco LLC案[5]和Jack Henry & Assocs., Inc. v. Plano Encryption Techs., LLC案[6]);专利权人亲自或者通过律师/代理人等其它方式进入法院所在州向被控侵权方展示相关专利的技术,与被控侵权方讨论侵权主张(Xilinx, Inc. v. Papst Licensing GmbH & Co.案[7]和Apple Inc. v. Zipit Wireless, Inc.案[8])等;针对法院所在州被控侵权方商业活动的非司法维权行为等(Campbell Pet Co. v. Miale案[9]),则也会满足最低程度的联系之要求。但是,即使上述“最低程度的联系”要件被满足,法院也通常会结合被告的主张及具体案件事实,考虑和权衡各种利益,进一步认定行使管辖权是否合理且公平。
对于专利权人而言,其可主张,被控侵权方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的法院不具有管辖权,进而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或者将案件移送至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因此,被控侵权方在选择管辖法院时,其应充分考虑该法院对专利权人建立特殊属人管辖权是否合理且公平,避免其提起的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被法院驳回。
二、美国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被受理的前提条件——“实际争议”
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的规定,联邦法院仅能受理具备“案件”(Cases)或“争议”(Controversies)特点的诉讼案件(此为宪法所规定的最低要求),而不能就假设性问题出具意见。案件须具备以下条件,方能满足“案件”或“争议”的要件:(1)存在“实际争议”:各方当事人之间应存在法律关系相关的“实际争议”;(2)针对双方的“争议”,司法机关应能够提供某种有效的救济(Aetna Life Ins. Co. v. Haworth案[10])。鉴于此,为了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被控侵权方应证明其与专利权人之间存在“实际争议”,且将该“争议”诉至法院可获得有效救济。
关于被控侵权方与专利权人之间是否存在“实际争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取“全情测试法”(“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test),即法院会综合案件事实判断在具有对立法律利益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争议”,且该“争议”是否具有足够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并足以支持作出确认不侵权之判决(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案[11])。在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被许可人认为其产品未侵犯专利权人的涉案专利权利,其无须先终止许可协议、而后再寻求针对专利的确认不侵权之判决。因此,被许可人可在维持许可协议有效的同时,请求法院确认其产品不侵犯专利权。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在认定是否存在“实际争议”时具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其通常会综合考虑以下事实:(1)专利权人过去就涉案专利针对原告或第三人的诉讼情况。若此前的诉讼历史不涉及涉案专利,则无法单独创造现实和紧迫的“争议”,在认定是否存在“实际争议”时,法院仅在该事实上赋予最低的考量权重(Prasco, LLC v. Medicis Pharmaceutical Corp.案[12]);(2)专利权人是否向原告提供专利许可,并且要求限期答复等;(3)专利权人是否有对侵权行为的具体指控等。法院认为,如果专利权人没有采取积极行动,仅因被控侵权方获悉专利权人专利的存在,或者主观认为具有侵犯该专利的风险,通常不会认定构成“实际争议”(SanDisk Corp. v. STMicroelectronics, Inc.案[13]);(4)专利权人面对原告不起诉承诺(covenant not to sue)或暂缓起诉协议(stand-still proposal)等的态度。法院认为,若专利权人仅拒绝签署不起诉承诺或暂缓起诉协议,但无其他积极采取的行为(affirmative actions),则不足以认定具有“实际争议”(National Presort, Inc. v. Bowe Bell + Howell Co.案[14])。但是,即使专利权人签署了不起诉承诺,若该承诺针对被控侵权方过去的行为,而不延伸至现在及将来被控侵权方生产的产品,则仍可能被认定构成“实际争议”(Revolution Eyewear, Inc. v. Aspex Eyewear, Inc.案[15]);(5)专利权人与被控侵权方的关系等。法院认为,相较于专利权人系非专利实施主体而言,若专利权人与原告系竞争对手,双方更有可能采取交叉许可等方式解决,从而降低“实际争议”产生的风险(Hewlett-Packard Company v. Acceleron LLC案[16]);(6)一事不再理效力。专利权人的侵权主张被法院驳回,且具有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原告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将无法满足“实际争议”(Gen Protecht Grp, Inc. v. Leviton Mfg. Co.案[17]);(7)被控侵权方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与专利权人救济和保护专利权的时间间隔。法院认为,若专利权人救济和保护专利权的相关情形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则即使被控侵权方未在专利权人救济和保护专利权后立刻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也不能否定被控侵权方与专利权人之间仍存在“实际争议”(3M Co. v. Avery Dennison Corp.案[18])等;(8)其他,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人的商业模式。法院认为若专利权人的商业模式还未成熟,则更有可能不提起诉讼,从而不足以认定构成“实际争议”。
因此,专利权人曾向被控侵权方发送警告函,威胁将针对其提起侵权诉讼;或者,专利权人针对被控侵权电商在电商平台上提起了侵权投诉。这些情况下,被控侵权方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讼的,都可满足上述提到的“实际争议”之要件。但是,若此“争议”来自一方当事人之假设的、臆想的,或是一方当事人虚拟得出的,其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讼就不能满足“实际争议”之要件。换言之,若在无明确纠纷存在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仅为了挑战专利稳定性或寻求法院对其产品是否落入某专利的保护范围进行评估(即寻求从法院处获得法律意见)之目的,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讼的,法院将因该案件不满足“实际争议”之要件的原因而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不过,若一方当事人仅从专利权人处收到了一封友善地邀请该方洽谈专利许可的函件,且函件中并未明确指出该当事方生产或销售产品的行为构成对专利权人的侵权呢?在此种情况下,该当事方能否在尚未回复专利权人的情况下就直接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讼呢?笔者认为,如上所述,此种情况下,“实际争议”之要件尚未被满足,该当事方提起的诉讼也有较大可能将会被法院裁定驳回。
对于专利权人来说,其可在被诉的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讼中主张,被控侵权方提起的诉讼不满足“实际争议”之要件,进而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提起的诉讼。这是专利权人可针对原告提出的一项反驳理由。因此,在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讼前,原告需仔细评估其与专利权人之间是否存在满足美国法要求的“实际争议”。若该“争议”仅为虚拟的、主观臆断的、假设存在的,或者该“争议”仅是为了寻求法院对特定法律问题作出评估意见而提起的,这都不满足美国法上对“实际争议”的要求,以此提出的诉讼将被法院裁定驳回。
三、美国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诉状充分性
被控侵权方在美国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时,除需要证明其与专利权人之间存在“实际争议”外,还需要确保其诉状符合充分性的要求,否则,若专利权人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b)(6)条的规定,向法院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申请,该申请将有可能被法院裁定批准,即,原告提起的诉讼将可能被裁定驳回。在Bell Atlantic Corp. v. Twombly案[19]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诉状充分性的判断原则:(1)诉状不能仅以结论性陈述为支撑,对诉因要件进行空洞复述;(2)原告需在诉状中陈述合理主张(法院通常会结合具体案件背景,并运用司法经验和常识进行分析)(Ashcroft v. Iqbal案[20])。
具体而言,在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中,被控侵权方需:(1)明确涉案专利;(2)详细阐述其主张未侵犯涉案专利的产品或行为,避免宽泛指定(Wistron Corp. v. Phillip M. Adams & Associates, LLC案[21]);(3)对于每一项主张不侵权的专利权利要求,提供简短、清晰且非结论性的陈述(Comcast Cable Communications LLC, v. OpenTV, Inc.案[22]),说明为何被控侵权产品不满足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一个或多个技术特征。
四、美国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中关于“侵犯专利权”的证明责任
在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中,由被控侵权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专利权人之间存在“实际争议”。但是,关于“侵犯专利权”的证明责任,目前美国司法实践中认为,应由专利权人承担举证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即,专利权人需要说服事实认定者(法官或陪审团)相信其主张(被控侵权方侵犯其专利权)的真实性。
在Medtronic, Inc. v. Mirowski Family Ventures案[23]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考虑到如下因素,在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中,专利权人就侵犯专利权承担举证责任:第一,专利权人(而不是本案中作为原告的被许可人)通常承担证明侵权成立的举证责任。第二,美国《宣告式判决法》(Declaratory Judgment Act, 28 U.S.C. § 2201)仅具有程序性效力,不改变实体权利。第三,举证责任属于诉讼请求的实体性要素,若仅因诉讼形式为确认不侵权之诉而将举证责任转移至被控侵权方承担,则可能会与后续侵权之诉在认定是否构成专利侵权上产生冲突,进而导致法律不确定性。第四,让被控侵权方承担其不侵犯专利权这一消极事实的举证责任,会使诉讼复杂化。相较于被控侵权方,专利权人显然更加清楚和有能力指出被控侵权产品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侵害涉案专利权。第五,举证责任转移会增加被控侵权方的负担,违背《宣告式判决法》的立法目的,即,缓解被控侵权方因专利权人的诉讼威胁而陷入在“放弃自由使用被诉侵权商品”与“冒险继续使用而面临被诉侵权风险”之间选择的困境。
五、美国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强制侵权反诉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3(a)条规定,如果反诉与本诉源于同一交易(transaction)或事件(occurrence),则该反诉具有强制性。Wright教授指出,满足以下任意一个条件,则该反诉具有强制性:(1)本诉与反诉所涉事实与法律问题是否基本一致;(2)若无强制反诉规则,一事不再理效力是否阻却后续就反诉诉求另行起诉;(3)支持或反驳本诉与反诉的证据是否实质性相同;(4)本诉与反诉是否存在逻辑关联。[24]在Vivid Technologies, Inc. v. American Science & Engineering, Inc.案[25]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认定,在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中,针对相同涉案专利的专利侵权反诉完全符合上述Wright教授提出的全部4项条件(反诉与本诉所涉专利相同,通常会认定反诉与本诉源于同一事实)。在Genentech, Inc. v. Eli Lilly and Co.案[26]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指出,在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中,被告必须提出专利侵权反诉,否则将永远丧失提出该反诉的权利。在Polymer Industrial Products Co. v. Bridgestone/Firestone, Inc.案[27]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还认为,针对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提出的专利侵权反诉属于强制性反诉,如果未及时提起侵权反诉将视为永久放弃提出专利侵权反诉之权利,其后续也不得就相同的诉求提起独立的诉讼。
此外,关于提起反诉的时间要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认为提起反诉的时间要求属于法院的合理自由裁量权范围[28],法院有权酌情允许被告在提交答辩之前或之后提起反诉[29],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反诉的迟延是否给另一方造成损害等因素。如果反诉的迟延已经给另一方造成损害,法院会根据懈怠原则(doctrine of laches)禁止提起反诉[30]。因此,专利权人若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侵权反诉,则可能会因过分迟延而被法院禁止提出,甚至后续不得就相同的诉求提起独立的诉讼。
六、美国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与美国多方复审专利无效程序的衔接
《美国法典》第35卷第315(a)条(35 U.S.C. § 315(a))规定,若在提交美国多方复审专利无效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以下简称“IPR程序”)申请前,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已经提起民事诉讼挑战专利权利要求的有效性,则该IPR程序不会予以立案。但是,申请人提起的挑战专利权利要求的有效性的反诉不属于前述民事诉讼的范围。
被控侵权方在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同时,通常会同时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此时,被控侵权方将无法再提起IPR程序,即无法通过IPR程序将涉案专利认定无效。即使被控侵权方后续自愿撤销或修改起诉状以删除专利权无效的主张,也无法再提起IPR程序。若被控侵权方在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提起诉讼时未主张涉案专利无效)后,专利权人针对被控侵权方提起侵权反诉,而被控侵权方针对专利权人的反诉进行答辩,届时才提出对专利有效性的质疑,则不会影响被控侵权方后续对该专利提起IPR程序(Epic Games, Inc. v. Acceleration Bay LLC案[3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被控侵权方不能随意在反诉答辩中主张非涉案专利无效,该种主张本质为针对该非涉案专利提出确认专利权无效之诉,视为“提起民事诉讼挑战专利权利要求的有效性”,被控侵权方将无法再对该非涉案专利提起IPR程序[32]。
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相比IPR程序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被控侵权方可以选择在对其相对有利的管辖法院审理纠纷。第二,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中,专利权人提起侵权反诉,被控侵权方在侵权反诉答辩中提出专利无效的理由包括可专利性(35 U.S.C. § 101)、新颖性与占先(35 U.S.C. § 102)、非显而易见性(35 U.S.C. § 103)以及专利申请文件书面描述要求和可实施性要求(35 U.S.C. § 112)(Epic Games, Inc. v. Acceleration Bay LLC案[33]),而在IPR程序中主张专利无效的理由仅限于新颖性与占先(35 U.S.C. § 102)和非显而易见性(35 U.S.C. § 103)。而IPR程序相比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具有以下优势:第一,IPR程序进展更快,一般情况下,IPR程序通常会持续18个月(此期限还可以再延长6个月,但此延长期很少出现),而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大概会持续25-30个月,诉讼成本非常高昂。第二,在IPR程序中就专利无效承担的举证责任轻于在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的侵权反诉答辩中提出专利无效的举证责任,前者的举证标准是“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标准,而后者的举证标准是“明确并有说服力”(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标准。
因此,对于被控侵权方而言,一项可行的策略是优先在相对有利的管辖法院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在此阶段,可暂不主张涉案专利无效,以避免因在联邦地区法院诉讼中挑战专利有效性后,基于《美国法典》第35卷第315(a)条导致后续提起IPR程序时面临不予立案的风险(2025年上半年,IPR程序被不予立案的案件比例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待专利权人提出侵权反诉后,被控侵权方可选择在反诉的答辩中主张涉案专利无效,或单独提起IPR程序。这一策略既能保留通过诉讼和IPR程序双重途径挑战专利有效性的可能性,又能增加被控侵权方后续与专利权人谈判时的筹码。
总之,在面对专利权人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提起专利侵权投诉、发送侵权警告函等情形时,主动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是被控侵权方可采取的有效应对策略之一。如前述分析,被控侵权方需首先评估是否存在“实际争议”。在满足该前提后,应审慎选择对己方有利的具有事项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的法院,并依据该法院适用的诉状充分性标准准备起诉状,避免被法院驳回起诉。此外,为了避免被控侵权方后续提起IPR程序无法被立案的风险,被控侵权方在提起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时可暂不主张涉案专利无效,而将该主张延后至对专利权人侵权反诉的答辩阶段或后续提起的IPR程序中提出。
注释:
[1] 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陪审团成员技术背景扎实,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诉讼程序推进迅速,被称为“火箭法庭(Rocket Docket)”。
[2] See Radio Systems Corp. v. Accession, Inc., No. 10-1390 (Fed. Cir. 2011).
[3] See Red Wing Shoe Company, Inc. v. Hockerson-Halberstadt, Inc., 148 F.3d 1355 (Fed. Cir. 1998).
[4] See Burger King Corp. v. Rudzewicz, 471 U.S. 462 (1985).
[5] See Trimble Inc. v. Perdiemco LLC, 997 F.3d 1147 (Fed. Cir. 2021).
[6] See Jack Henry & Assocs., Inc. v. Plano Encryption Techs., LLC, 910 F.3d 1199 (Fed. Cir. 2018).
[7] See Xilinx, Inc. v. Papst Licensing GmbH & Co., 848 F.3d 1346 (Fed. Cir. 2017).
[8] See Apple Inc. v. Zipit Wireless, Inc., No. 2021-1760 (Fed. Cir. 2022).
[9] See Campbell Pet Co. v. Miale, 542 F.3d 879 (Fed. Cir. 2008).
[10] See Aetna Life Ins. Co. v. Haworth, 300 U.S. 227 (1937).
[11] See 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 549 U.S. 118 (2007).
[12] See Prasco, LLC v. Medicis Pharmaceutical Corp., 537 F.3d 1329 (Fed. Cir. 2008).
[13] See SanDisk Corp. v. STMicroelectronics, Inc., 480 F.3d 1372 (Fed. Cir. 2007).
[14] See National Presort, Inc. v. Bowe Bell + Howell Co., 663 F. Supp. 2d 505, 510-12 (N.D. Tex. 2009).
[15] See Revolution Eyewear, Inc. v. Aspex Eyewear, Inc., 556 F.3d 1294, 1297-1300 (Fed. Cir. 2009).
[16] See Hewlett-Packard Company v. Acceleron LLC, No. 1:2007cv00650 (D. Del. 2009).
[17] See Gen Protecht Grp, Inc. v. Leviton Mfg. Co., No. CIV 10-1020JB/LFG, 2012WL1684573 (D.N.M. 2012).
[18] See 3M Co. v. Avery Dennison Corp., No. 11-1339 (Fed. Cir. 2012).
[19] See Bell Atlantic Corp. v. Twombly, 550 U.S. 544 (2007).
[20] See Ashcroft v. Iqbal, 556 U.S. 662 (2009).
[21] See Wistron Corp. v. Phillip M. Adams & Associates, LLC, 2011 WL 1654466 (N.D.Cal. 2011).
[22] See Comcast Cable Communications, LLC v. OpenTV, Inc., 319 F.R.D. 269 (N.D.Cal., 2017).
[23] See Medtronic, Inc. v. Mirowski Family Ventures, LLC, 571 U.S. 191 (2014).
[24] See Charles Alan Wright, Arthur R. Miller & Mary Kay Kane,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 1410, at 52-58 (2d ed.1990).
[25] See Vivid Technologies, Inc. v. American Science & Engineering, Inc., 200 F.3d 795 (Fed. Cir. 1999).
[26] See Genentech, Inc. v. Eli Lilly and Company, 998 F.2d 931 (Fed. Cir. 1993).
[27] See Polymer Industrial Products Co. v. Bridgestone/Firestone, Inc., 347 F.3d 935 (Fed. Cir. 2003).
[28] See Clay v. Pepper Construction Co., 205 Ill. App. 3d 1018 (Ill. App. Ct. 1st Dist. 1990).
[29] See Benckendorf v.Burlington N. Railroad,112 Ill. App. 3d 658 (Ill. App. Ct. 2d Dist. 1983).
[30] See Beckham v.Tate, 61 Ill. App.3d 765 (Ill. App. Ct. 5th Dist. 1978).
[31] See Epic Games, Inc. v. Acceleration Bay LLC, 2020 WL 1557436 (N.D.Cal. 2020).
[32] See IPR2017-01995, Paper 77, 6-7.
[33] See Epic Games, Inc. v. Acceleration Bay LLC, 2020 WL 1557436 (N.D.Cal.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