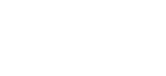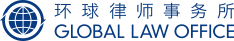近年来,我国证券监管机构与司法机关全面落实“零容忍”的要求和理念,持续加大对证券违法犯罪活动的惩治力度。2025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举行“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葛晓燕在通报证券犯罪检察工作的主要情况时表示,2022年至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证券犯罪366件、1011人,起诉案件数、人数年均增长30.5%、16%,其中,起诉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交易类案件共284件、790人。[1]可见,在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下,内幕交易犯罪已成为重点查处对象。内幕信息作为内幕交易犯罪的核心构成要件,是区分合法交易行为与内幕交易行为的关键。因此,深入研究内幕信息的理论内涵,重新检视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内幕交易犯罪,以及在辩护实务中的有效应对和化解刑事法律风险,均具有重大意义。
一、域内外证券内幕信息认定标准的立法模式
(一)内幕信息的内涵与范围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息经济,掌握信息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把握财富。事先知悉信息者可以基于信息优势进行预先操作,获得经济利益或避免经济损失,但这无异于将市场中本应属于公众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占为己有,或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损失转嫁他人,实际上是对其他证券市场主体经济利益的剥夺。[2]因此,各国刑法规制内幕交易犯罪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维护证券交易过程中信息的平等性,确保所有投资者在相同的信息基础上进行交易,进而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秩序,这也是美国早期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的理论基础。
但是,并非所有影响股票价格的信息或作为证券投资者判断依据的信息均可以被认定为内幕信息。有学者认为,根据来源的不同,影响股票价格的信息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内部信息”(inside information),即来源于公司内部,涉及公司的财务和业务,直接与发行公司的资产或盈利能力相关的信息。例如,有关公司的经营业绩、内部机构运行、资产和收入、高级职员的变动等的信息。二是“市场信息”(market information),指并非来源于发行公司自身,与其资产或盈利能力没有直接关系,但能够对其证券价格的市场供求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例如,投资顾问即将作出“买进”该公司证券的建议、公司大股东正在寻求减少持股、一项公开收购该公司证券的要约将要发出,等等。三是“外部信息”(outside information),指与发行公司及其证券并无直接关系,因政府作出重大政策或其他公权力行使而对整个证券市场供求产生影响的信息。例如,中央银行调整贴现率等影响利率升降的具体措施,政府发布禁止某类产品销往特定国家的法规,法院作出有关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判决,等等。[3]
也有学者将作为证券投资者判断依据的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信息,即发生在证券发行人外部的信息,诸如国家相关法律政策的变化、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前景、某一行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银行利率的变化、一定时期的证券发行量和交易量等。这类市场信息可以影响证券的市场价格,但其对市场上的证券价格只具有“类的决定性”,即对证券市场的总体价格或者某一类证券的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另一类是私有信息,即发生在证券发行人内部的信息,主要是证券发行人的经营状况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主体的有关信息。私有信息对市场上的证券价格具有“种的决定性”,即对某一种证券的市场价格产生影响,是市场上不同证券之间产生价格差别的主要决定因素。[4]
总体而言,无论采用何种分类方式,对于与“发行人经营、财务”无直接关系,但足以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政府政策信息,能否纳入内幕信息的规制范畴,是界定内幕信息外延的关键问题,究其本质,该问题的核心在于内幕信息是否应具备“相关性”要素。
(二)域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模式
基于对内幕信息范围和“相关性”要素的不同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出不同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可以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绝对肯定“相关性”模式、相对肯定“相关性”模式、否定“相关性”模式。
1. 绝对肯定“相关性”的立法模式
英国在1993年《刑事审判法》(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第56(1)(a)条明确规定:内幕信息应当与某一证券或证券发行人、或特定种类的证券或证券发行人相关,而不是与证券或发行人的整体相关,从而将外部信息排除在内幕信息范围之外。[5]日本则在《金融商品交易法》(日语称“《金融商品取引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二款对上市公司的重要事项进行了明确的列举,其中包含重大经营决议、股份变动、公司合并、分离等,将内幕信息的范围严格限定为与公司经营管理、业务运作、财务状况等相关的事项内,而不包含宏观经济政策、国际政治事件等信息。[6]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证券法》(Securities Act R.S.O.)中亦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任何与发行人存在特殊关系的人或公司,在知悉有关该发行人的重大事实(material fact)或重大变化(material change),但该等信息尚未普遍披露的情况下,不得买入或卖出该发行人的证券”。该法的第一条对“重大变化”和“重大事实”的含义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重大变化”所具体列举的事项均与发行人业务、经营、资本及管理人员变动相关,“重大事实”则是指除发行人内部“重大变化”之外的其他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客观事实,结合第七十六条的规定,“重大事实”也应严格限定于“与发行人相关”的范围内。[7]
2. 相对肯定“相关性”的立法模式
我国香港地区《内幕消息披露指引》第十三条将内幕信息界定为:“关于(I)法团的;(II)法团的股东或高级人员的;或(III)法团的上市证券的或该等证券的衍生工具的”重大未公开信息,并在第三十五条对“可能构成与法团有关的内幕消息的例子”进行了列举,均为与发行公司经营、财务有关的事项,而不涉及影响证券市场整体的外部信息或政策信息,这一规定与英国相似。但是,根据第三十六条的说明,第三十五条的列举并非封闭列举,第三十六条规定“如某项事件或某组情况并未出现在清单上,并不代表其绝非内幕消息,反之,载于清单上的时间或情况亦不一定自动成为内幕消息。决定有关信息或资料是否属于内幕消息,须视乎其重要程度而定”。[8]这意味着在具体的个案中,存在法官将与法团间接有关的“政策信息”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可能。相较于香港,欧盟对于内幕信息“相关性”标准的规定更为开放。尽管欧盟《禁止市场滥用指令》第1.16条对于内幕信息范围的界定提及了“相关性”的要素,但该条款同时也对“相关性”的含义进行了扩张,明确将央行有关利率的决定、政府税收、行业监管等外部信息均纳入了内幕信息的范围。[9]
3. 否定“相关性”的立法模式
采用否定模式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在Blyth & Co.案中,一家经纪商基于从联邦储备银行员工处获得的机密财政部信息进行政府债券的交易,在此情景下,合议庭将该交易裁定为对内幕信息的“不当使用”,认为该行为违反了《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的第10(b)和10(b)-5规则。[10]法官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Cady, Robert案判决所确立的规则扩张适用至从政府内部人员获取信息的人员(tippee)范围。[11]在Vincent F. Chiarella, Petitioner, v. United States. 案中,该观点得以重申,法官认为,从字面意义上解读,第10(b)和10(b)-5条款适用于参与任何欺诈计划的任何人,并否定了国会提出的内幕信息仅限于“企业内部人”交易或与“企业信息”相关的观点。[12]可见,在美国,构成“内幕信息”并不要求该信息必须与发行人公司具有“相关性”,利用政府信息等外部信息进行交易亦可能构成内幕交易。
(三)我国内幕信息认定标准的立法现状
与采用特别刑法规制证券类犯罪的国家和地区不同,我国仅在《刑法》的第一百八十条对内幕交易行为进行了较为简单的罪名设置和罪状描述。《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这一条款是典型的“空白罪状”,即条文本身对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未进行明确表述,需具体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判断。而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中,仅有《证券法》的第五十二条对内幕信息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发行人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发行人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信息,为内幕信息”,本条系对内幕信息含义的一般性规定。同时,《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作为引致条款,将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指向《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相应条款采用“列举+兜底条款”的方式,具体、明确地列举了涉及内幕信息的重大事件,且该重大事件均与“发行人的经营、财务”直接相关。
从上述规定中不难发现,我国的立法未绝对肯定“相关性”作为内幕信息认定标准中必要且独立的构成要素。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释义》中,在具体阐述《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的含义时,认为“内幕信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涉及发行人的经营、财务状况的信息,这类信息是投资者判断发行人发展前景、确定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的投资价值、作出投资决策的必要依据,是内幕信息的最典型情形。另一类是对发行人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这类信息有的来源于发行人内部,也有的来源于发行人外部,这些信息虽不涉及发行人的经营、财务状况,但是传播开来,会对证券的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13]据此说明,立法工作参与者可能倾向于将“相关性”作为非必要的审查要素。
二、当前内幕信息认定标准的理论争鸣与司法分歧
尽管立法工作参与者在相关著作中阐述了其对《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的理解,但目前有关机关尚未出台具有法律效力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内幕信息的“相关性”是否属于必要且独立的要素,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争议。
(一)内幕信息认定标准的学说之争
学理上而言,基于不同的理解,学者们对于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分别提出了“两标准说”、“三标准说”、“四标准说”和“修正的两标准说”。支持“两标准说”的学者认为,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为“未公开性”和“重大性”;“三标准说”则认为,在“未公开性”和“重大性”的基础上,内幕信息的界定标准还应包含“相关性”;对于“三标准说”,另有学者主张,认定内幕信息的三个标准应为“未公开性”、“重大性”和“确定性”;“四标准说”则认为,内幕信息应具备上述全部要素和特征,即某一信息在同时满足“未公开性、”“重大性”、“相关性”和“确定性”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内幕信息。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修正的两标准说”,即认为内幕信息的认定应以“未公开性”和“重大性”为核心,将“相关性”和“确定性”等要素纳入“重大性”的判断中。[14]可见,理论界对于“未公开性”和“重大性”标准并无争议,主要争议焦点为“相关性”和“确定性”能否作为认定内幕信息的必要要素和独立标准。
肯定“相关性”要素的学者认为,尽管国家政策变化必然对证券价格产生系统性影响,然而,政策变化由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掌握,非由企业掌握和控制,此类信息不具有特定性,不属于特定知情人员独占的信息,《证券法》无力加以调整。[15]亦有学者认为,虽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以及政治信息的发布都会影响证券价格的变动,但该影响是全盘性的,并非针对某一或者某些证券,且政策信息对证券交易的影响并不稳定,预先获悉该信息的人员可能无法通过具体证券价格的涨落获取利益,因此,尽管可能政策信息比某一或者某些具体信息对证券价格更具影响力,但欠缺“内幕操作性”,如将其归为“内幕信息”,这是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司法部门效能的“过度”期待。[16]同时,也有刑法学者认为,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内幕信息”的范围较窄,仅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等内部信息,并未将国家经济政策、宏观信息等外部信息纳入其中,基于此规定,该学者认为我国法律中的内幕信息只能是与公司相关的经营、财务等信息。[17]
否定“相关性”要素的学者则认为,“相关性”不具有独立作为内幕信息认定要素的价值。有学者认为,在对内幕信息“重大性”特征的判断过程中,已经伴随着对“相关性”特征的判断,重大性与相关性已经融为一体了;而且某些不与公司的财务、经营相关的信息并非不重要,其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可能会通过其他的间接方式体现出来,如果以“相关性”来判断该类信息的话,可能就会将其排除在外,此时明显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制。[18]亦有学者肯定此类观点,其认为,“相关性”不是独立的内幕信息构成要素,而应作为重大性的下位概念,纳入内幕信息重大性和未公开性的“两标准说”中进行理解。[19]在此基础上,有观点认为,即使是采用相关性要素界定内幕信息的立法例,为有效打击内幕交易,也很难抑制将内幕信息范围扩大化的需求,因此,在信息平等理论的视域下,应将外部信息纳入内幕信息的范围。[20]
(二)司法实践中关于内幕信息认定标准的争议
在内幕交易犯罪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公诉机关还是法院,对于内幕信息“相关性”的问题均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221号指导性案例“蒋某某内幕交易案”中,裁判要旨认为,“认定内幕信息,应当根据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从“对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与“尚未公开”两方面作实质判断。对于证券法所列重大事件以外的信息,符合前述规定要求的,依法认定为内幕信息”。[21]在具体个案中,部分公诉机关人员亦认为,依据《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即使某一信息不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列举的内幕信息类型,仍可以依据《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一般性规定进行认定,即只要该信息对证券价格具有重大影响,就可以认定为内幕信息,无需再审查该信息是否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具有“相关性”。北京高院曾在“某证券乌龙指案”中作出类似的判决,法院认为,“对于本案错单交易信息是否属于《证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所规定的内幕信息问题。《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现行《证券法》已改为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该条第二款在列举与发行人自身相关的信息为内幕信息后,明确规定内幕信息还包括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现行《证券法》已将表述改为“法定”)。由此可见,内幕信息的认定必须是对证券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且尚未公开的信息,法律上并未明确限定于与发行人自身相关的信息”。[22]
但是,上述判决一经作出,便有肯定“相关性”要素的学者提出质疑,其认为,证券市场股票的价格表面上受投资者资金及交易量的影响,但背后真正起决定因素的是公司本身经营的好坏和效益的高低,公共信息对证券价格仅有“类的决定性”,而与发行人相关的私有信息才对证券价格具有“种的决定性”。因此,《证券法》规制的信息应是是证券市场上的私有信息,《证券法》规制的“内幕信息”也主要来源于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23]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祝二军法官持类似的观点,其认为,“内幕信息必须与其证券在证券市场交易的公司有关,而且主要与公司的经营、财务有关。就是说,公司是内幕信息的源泉。凡是不涉及公司的信息,即便再重要,与证券价格再有影响,也不属于内幕信息的范围。据此,诸如宏观经济形势的好坏,利率的升降,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证券交易税费的调整,等等,都不属于内幕信息的范围”。[24]同时,亦有部分检察机关认同内幕信息应当具有“相关性”的观点,例如北京市检三分院在普法宣传文章中认为,“相关性主要是指内幕信息产生和来源于上市公司,既可以体现在与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相关,也可以体现在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高管人员相关等。对此,我们可以对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中的未公开信息,后者便是一种交易信息,不具有与发行人的相关性”。[25]
三、反思与重述:“相关性”应作为认定内幕信息的独立要素
从立法的演变过程而言,“相关性”在我国证券法律规定中的独立价值不断提升。对于内幕信息的范围,早期的法律文件(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现已失效)中规定为“本办法所称内幕信息是指为内幕人员所知悉的、尚未公开的和可能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重大信息”,且在该条款的具体列举中明确规定,“内幕信息”包括“可能对证券市场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国家政策变化”。之后,该法规被2005年公布的《证券法》代替,经过多次修订,最新的2019年《证券法》中,将内幕信息的范围限定为“涉及发行人的”信息,明确了内幕信息的“相关性”要素,即内幕信息是指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本身密切相关的财务或经营方面的信息,并以此与其他未公开的市场信息相区分,不再将国家政策等外部信息纳入内幕信息的范畴。[26]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而言,“相关性”应理解为与“重大性”并列的内幕信息构成要素。尽管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证券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认为“或者”表示的是“选择关系”,但这一解释可能产生以下结论:“相关性”与“重大性”仅需满足其中之一,即只要是涉及发行人的经营、财务的尚未公开信息,无需再进行“重大性”之审查,亦可构成内幕信息。这一结论的合理性存在重大疑问,上市公司更换非核心高管的信息也属于涉及发行人经营、财务的尚未公开信息,但可能对股价几乎无法造成重大影响,显然不能认定为内幕信息。因此,此处的“或者”不应理解为“选择关系”,而应理解为“并列关系”,即只有将二者分别作为均为独立的判断要素,才能准确认定内幕信息的范围。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在《刑法》中,应以“相关性”区分“内幕信息”与“未公开信息”;在《证券法》中,对于采用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认定的内幕信息,应当与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所列举信息具有相当性。与美国的立法例不同,我国在《刑法》中明确将“内幕交易罪”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区分为两种行为、两个罪名,因此,在打击范围上,并不会因为将与发行人无关的外部信息排除在内幕信息之外,而导致《刑法》规制效力的不当下降。反之,如将国家政策、银行汇率等外部信息纳入内幕信息的范围,则可能导致刑事处罚在罪名上的混淆。此外,尽管《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均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但该兜底条款亦不能任意解释。经笔者检索,目前暂未发现证监会就相关事项有明确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司法机关适用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一般性规定或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的兜底性规定,均不应任意解释,而须与法律明确列举的重大事件具有相当性。
四、内幕信息“相关性”要素的现实价值与法治意义
在证券市场中,充斥着各类交易信息,“合法信息”与“内幕信息”、“合法交易行为”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往往可能仅“一步之遥”。“相关性”要素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划定内幕信息的范围,排除过于宏观或抽象的信息,防止将过于宽泛的经济类信息纳入内幕信息之中,保障合法信息的正常流通。在司法实践中,“相关性”和“重大性”均是界定内幕信息性质的重要要素,对于公诉机关和法院在刑事程序中准确认定内幕信息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重视和强调“相关性”要素的必要性和独立性,更有利于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和《证券法》相关条款时进行“要素式”的审查,精准定位内幕信息的边界,避免将无辜的投资者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
总之,当前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行动,在维护证券市场公平交易、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和成效。但是,如前所述,在部分个案中,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争议和问题。笔者认为,现行的《证券法》中,立法机关对于内幕信息的范围已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详细的列举,在此基础上,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活动,须充分考虑内幕信息认定标准的“相关性”要素,严格限制内幕交易处罚范围,以避免“司法激进主义”对上市公司、投资者等合法市场主体正常开展的业务产生影响和反噬作用,在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发展的同时,更好地维护民营企业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注释: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举行“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https://www.spp.gov.cn/spp/yfcydjzqwffzb/22xwfbh_sp.shtml。
[2] 赵姗姗:《法益视角下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的规范构造》,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第50页。
[3] 参见张小宁:《证券内幕交易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4] 陈洁、曾洋:《对“8·16光大事件”内幕交易定性之质疑》,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1期,第185-186页。
[5] 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 §56(1)(a).
[6] 《金融商品取引法(昭和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法律第二十五号)》第一百六十六条。
[7] Securities Act R.S.O. 1990, §1, 76.
[8] 参见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内幕消息披露指引》,2012年6月,第13条、第35条、第36条。
[9] See THE COMMITTEE OF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ORS, Market Abuse Directive Level 3-second set of CESR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 on the common operation of the Directive to the market, 2007, §1.16.
[10] Blythe & Co., 43 SEC 1037, 1040 (1969).
[11] Cady, Roberts, 40 S.E.C. 907, 911–12 (1961).
[12] Vincent F. Chiarella, Petitioner, v. United States., 445 U.S. 222 (1980).
[13] 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90页。
[14] 参见江海洋、魏书敏:《内幕交易罪之内幕信息的界定:从静态形式标准到动态综合认定》,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第108页。
[15] 参见叶林:《证券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页。
[16] 同注③,第186-187页。
[17] 参见赵长青主编:《刑法新观念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18] 闻志强:《“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和司法适用分析》,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1-132页。
[19] 沈伟、陈徐安黎:《行政交叉视角下内幕信息刑法认定的理论透视与规则重构》,载《证券市场导报》2023年12月号,第46-47页。
[20] 同注⑭,第109页。
[2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25年第2号(总第205号)第 41-43 页。
[22] (2015)高行终字第943号案判决书。
[23] 同注4。
[24] 祝二军:《证券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25] 北京市检三分院:《券事检语|券事讲堂——什么是内幕信息?》,载“京检在线”公众号,2022年6月25日。
[26] 参见郭锋等著,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制度精义与条文评注(2019年修订版)》,第52条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