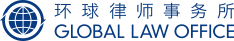2020年5月28日,讨论多年之久的《民法典》终于正式颁布,并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法典》第二编“物权”在吸纳与借鉴《物权法》与《担保法》项下的多数法律规定的同时,对于该等两部法律项下的部分规定亦进行了实质性修订,并新增了“居住权”等条款。经仔细研究,笔者发现,关于物上权利负担的流转规则,《民法典》在继承《物权法》与《担保法》的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故,笔者拟以此为题,就《民法典》项下物上权利负担流转规则的演进提出见解,以供读者参考。
一、物上权利负担流转规则的学理讨论
“权利负担”的概念脱胎于英美法系,主要指第三人对物的非直接支配性权利。中国法项下,典型的物上权利负担包括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虽然法学界对于物上权利负担流转规则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简称“消灭主义”或者“处置主义”(以下简称“消灭主义”),主张物上权利负担应于物的流转前“处置”;第二,简称“继受主义”,主张物上权利负担可随物的流转而由新的所有权人承继。
(一)物上权利负担应于物的流转前“处置”
主张“消灭主义”的观点认为,物上权利负担应于物的流转前“处置”。这种安排的优势在于:第一,物上权利负担项下权利人的权利可提前行使,避免因物的流转而给该等权利人行使权利带来任何不利影响;第二,新所有权人所受让的是不再负有权利负担的“完整”的物,一方面,使得新所有权人的买受意愿更强,另一方面,未来物流转时不再受权利负担的约束或影响。
但同时,“消灭主义”主张的劣势同样明显,即:第一,要求相关权利人在物流转时必须先行处置其上的“权利负担”,严重影响了物的流通性,甚至在物的价值低于其上权利负担项下债务的情况下,物的流通性几乎完全丧失,有悖于物尽其用的普世原则;第二,以担保物权为例,于物流转时强行处置其上的担保物权,无论是提前清偿债务(颠倒了担保物权与主债权的关系)还是提存(主要指担保人将担保物转让所得中对应主债务的部分交由法院或有关机关保存,待主债权到期后用于履行担保义务,本质上将物上担保强行调整为保证金担保)都损害了担保义务人的相关权利,因为,一方面,担保物权所担保的是主债权的顺利履行,属于主债权的从权利,那么在主债权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即因为担保物的流转而触发主债权提前清偿,实属本末倒置;另一方面,保证金担保与物上担保两者在意思表示上有明显的区别,因为担保物的流转而使得担保义务人必须强行改变其意思表示,本身就是对其意思自治的干预;第三,就用益物权而言,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是对于物的“占有、使用或收益”,与物本身联系的紧密程度明显超过与物的所有权人的联系,那么“消灭主义”所主张的,在物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仅因物的流转(物的所有权人产生变化)即导致物上用益物权必须被处置的观点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二)物上权利负担可随物的流转而“继受”
主张“继受主义”的观点认为,物上权利负担可随物的流转而由新的所有权人承继。“继受主义”主张的优势在于:第一,处置物上权利负担并非物流转的前提,使得物的流通性有所增强;第二,物上权利负担得以保留,使得相关权利人权利的行使更符合意思自治原则,较好地避免了外界的干预。
但“继受主义”也并非完全没有劣势,第一,物上权利负担的价值与未来的变化情况不易确定,这就导致带有权利负担的物的价值不易估算;第二,新所有权人所受让的是负有权利负担的物,使得原有物上权利负担项下法律关系复杂化,未来相关权利人行使权利时可能需要新所有人的配合。
二、民法典项下物上权利负担的主要流转规则
(一)用益物权流转规则的完善
《物权法》第162条规定,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地役权或者负担地役权的,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时,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宅基地使用权人继续享有或者负担已设立的地役权。而,《民法典》第378条将该条修订为“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地役权或者负担地役权的,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时,该用益物权人继续享有或者负担已经设立的地役权。”从条文比较中可以看出,《民法典》将“享有或者负担已经设立的地役权”的主体由特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宅基地使用权人拓展至用益物权人(不仅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宅基地使用权人,还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自然资源使用权人等等),进一步肯定了地役权流转采纳“继受主义”的主张,完善了物上用益物权流转规则。
(二)担保物权流转规则的突破
《物权法》第191条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结合上文,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物权法》的现行规定属于典型的“消灭主义”。而,《民法典》第406条将该条修订为“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从《民法典》第406条本身来说,所体现的是“继受主义”的主张。
经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关于抵押财产的转让,《民法典》与《物权法》设置了明显不同的规则。首先,《民法典》明确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抵押财产可以转让,且仅需通知抵押权人即可,无需经抵押权人同意,而《物权法》则规定,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仅在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情况下例外;其次,《民法典》明确规定,抵押权人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的前提为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而《物权法》则规定,无论何种情况下,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都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最后,《民法典》肯定了“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从上述变化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关于物上抵押权的流转规则,《民法典》舍弃了《物权法》中确立的“消灭主义”,而改为“继受主义”。
(三)物上租赁权流转规则的延续
《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谓“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基础。《民法典》第725条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从条文上来看,《民法典》在基本沿用《合同法》第229条精神的同时,也在该等条款的基础上作出发展,即不仅强调“租赁”,更强调“占有”。其实,在司法实践中,占有租赁物是主张“买卖不破租赁”的要件之一早已是业界的共识,此次《民法典》的出台,将该等共识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明确,本质上也是一种对于《合同法》项下物上租赁权流转规则的延续。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物上权利负担的流转规则,《民法典》相较《物权法》而言,体现出一种“消灭主义”向“继受主义”的过渡,强调以“物”为核心,而对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进行有限的突破,更体现对个人意思表示的尊重和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维护。但同时,与《物权法》采取的体例相似,《民法典》对于适用“继受主义”的物上权利负担仍采用列举的方式予以规定(例如,对于地役权、抵押权以及租赁权的流转均系以独立法条单项规定),而未对于权利负担进行概念界定和系统的区分适用,进而导致权利负担的内涵与外延仍有一定模糊性,而且在物上权利负担流转规则逐步明晰的同时,股权上权利负担的流转规则却似乎没有“与时俱进”,笔者将于后续的文章中进一步讨论权利负担的内涵与外延以及股权上权利负担的流转规则。